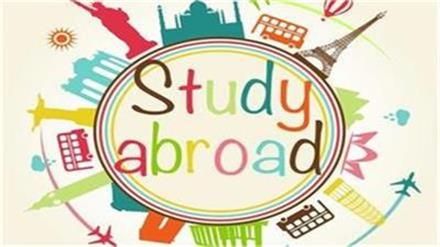出国留学,看似光环无限,其实背后的心酸苦楚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留学群来说说去美国交换留学居然被导师折磨,现在为国外孤儿拉琴。
2007年,当24岁的翁顺砚在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的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之时,他应该不会想到,十年后的菲律宾,会有一群异国孤儿因自己的琴声而重燃希冀。
作为一名远赴重洋交换学习的学生,那时的他,生活已被各种生物学实验所填满,最艰苦的时候,连续三个月每天都要工作15-16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而比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华人导师暴风骤雨般的谩骂攻讦。
翁顺砚说,去美国交换留学的经历既是一次磨难也是一次转机,从此让他彻底看清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也因为曾经身处困境,而对那些需要援手的人多了一丝悲悯与怜惜。
学了14年生物,最后竟然选择给外国孤儿拉琴?
他说,爱与温暖无国界
从生物学到音乐,这条路他走了14年
现任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和彩虹室内乐团的中提琴首席,同时也是自由职业的小提琴及中提琴老师,每一位听到翁顺砚这样做自我介绍的人,都会误以为他是“科班出身”的音乐人。
然而,他并不是。
这个能拉出动人乐曲的青年,在彻底投身音乐道路之前,已经读了整整14年的生物学。
对音乐的热爱,在翁顺砚很小的时候就已生根发芽。两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电子琴,四岁的时候开始学小提琴,不过这些,都只是“自己弹着玩”,还并没有纳入正式的人生规划。
在翁顺砚填报高考志愿那会儿,刚好赶上了克隆羊多莉的横空出世,这只寿命不算太长的绵羊,标志的是生物技术史上的重大飞跃。
于1996年7月5日诞生的克隆羊多莉
“那正是生物学吹得很热的时候,人人都在谈论克隆羊。好像选了生物,前途就会一片光明。”
在亲友的指导和劝解下,本来对音乐学院指挥系有些“想法”的翁顺砚还是听话地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生物学专业,并被顺利录取,从此开始了“在一条道上走到底”的生物学求学生涯。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翁顺砚在生物学这条路上走了整整14年,其实他早已察觉,人人都看好的热门专业,却未必适合自己。
翁顺砚觉得,自己的思维属于跳跃而发散的类型,相比较而言更加适合读文科,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打心眼儿里感到喜悦的选择。
既然早就发觉自己并非那么喜爱生物,为何不早早转换人生道路?何必苦苦撑着不放手?
面对这样的疑问,翁顺砚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和信念——也许把这条道路走完,也许拿到了这个专业的最高学位,他终有一天会发现生物的迷人之处,真心地爱上这门学科。不肯轻易认输的他,愿意坦然地接受这场考验。
然而,人生总是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顺遂,有时连“一条路走到底”都可能仅仅是一种幻想。
果然,在翁顺砚前往美国留学交换的那一年,无情的磨难与锤炼就让他认清了现实。
在美国遭遇打击,也收获温情与惊喜
在翁顺砚读到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能够跟着自己导师的一位朋友——一个来自美国大学的华人教授,前往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进行交换学习。
说是“交换”,实际上是协助教授在实验室内进行各种生物学实验,并按照要求完成研究工作。
翁顺砚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实验室
按照翁顺砚的描述,他很不幸地遇上了一位极为严苛的华人教授,在强度极高的实验室工作下,教授不断地给他这个硕士都没毕业的学生分配一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翁顺砚还清晰地记得,某天教授要求他独自完成一个实验,并且不允许他在网上搜集资料或求助同在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他看了一下实验的细节——完全是没有学过的“超纲内容”。
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下,他唯有硬着头皮往下做,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教授见状,并未耐心地对他进行指导,而是扯着嗓子开始谩骂。
翁顺砚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实验室
在突如其来的“愚蠢”、“像猪一样笨”的羞辱下,翁顺砚懵了,他未曾想过这些充满攻击性的词汇会出自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学教授之口。他很想解释,可对方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翁顺砚和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同学们在一块儿
后来,翁顺砚才慢慢明白,原来实验室里的同学们早就习惯了这位华人导师的做派,对于他动辄拍桌辱骂的行为,也早就见怪不怪。
《世界华人周刊》曾报道过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不少拥有着完美学历背景、不菲收入和光鲜亮丽头衔的海外高校导师,在留学生们心目中其实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压榨学生、出言辱骂乃至恐吓威胁,是这些导师的一贯作风。生活在他们阴影下的学生,有不少抑郁成疾,甚至选择了自杀身亡的绝路。
去年10月在金门大桥自杀身亡的中国留学生唐晓琳,在美国读博士已经读到了第七个年头。然而,据唐晓琳生前密友透露,她最终走上绝路,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导师对她不好”。
去年10月在美国自杀身亡的中国留学生唐晓琳
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海外高校中肯定存在着许多关心学生、受人爱戴的优秀导师,但翁顺砚这一年来遭遇“奇葩”导师的经历,已让他对生物学这个原本就不够热爱的学科丧失了激情。
在被不喜欢的专业和不友好的导师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选择去辛辛那提大学交响乐团的排练厅拉琴,用音乐来抚慰自己受伤无助的心灵,也就在那里,他遇见了如同亲人一般的美国挚友,收获了跨越国界的情谊。
翁顺砚和查尔斯、萨莉夫妇合影
查尔斯和萨莉夫妇俩,一个是大提琴家,一个是大管演奏家。对音乐同样的热爱让他们和翁顺砚这个中国小伙子慢慢走到了一起。
当他们知道翁顺砚在实验室的遭遇,对这位异国他乡来到美国生活的年轻人感到心疼不已。查尔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那样做是违法的!我很想帮助你,孩子,但我无能为力。”
不管怎么说,夫妇俩的存在还是让翁顺砚感到一丝家的温暖。他们也把翁顺砚当成儿子一般来对待,邀请他来做客、聚餐、合奏音乐……
每当在实验室受委屈的时候,他也会来到查尔斯和萨莉身旁,向他们倾诉心中的郁闷不快。
“如果没有他们时时拉我一把,我在美国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翁顺砚回忆道,“很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知道,其实善良不分国界。”
音乐的力量,就是能让人们的眼睛闪光
完成一年交换学习后的翁顺砚,由于回国后的读博经历也十分不顺,最终,他还是决定彻底放弃生物学,而开始把音乐当作全职的事业。
而他第一次接触公益,就是在上海城市交响乐团2009年的一次天使知音沙龙上——那是一个专门为自闭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组织的慈善公益平台,在那里,乐团演奏者会为自闭症孩子奏响乐曲,或是带着他们学习演奏,希望能够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感到一丝温暖与快乐。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母亲的眼神让他触动。
天使知音沙龙中的一位自闭症儿童母亲
当这位母亲看到自己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终于因美妙的乐曲而有了一些反应,甚至开始与外界的互动,她的眼神中写满了心酸和惊喜。
那个眼神让翁顺砚开始思考,当他自己身处磨难与困境之时,音乐曾是他的良药。那么对于那些同样面临绝望的人们,音乐意味着什么?
在更多的慈善尝试和公益实践中,他最终找到了答案——“音乐,能够让人们的眼睛闪光”。
自此,翁顺砚成了公益活动的“常客”。山村贫困儿童、自闭症患儿、医院里的孩子……他试着用一首首乐曲为他们送去希望与感动。
2013年,在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病患儿童演奏的活动中,他遇见了来自异国的一位朋友——日本钢琴家广濑清隆。这位年逾半百却至今独身的日本友人,也同样致力于用音乐的方式来做公益,用琴声来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
翁顺砚的日本友人广濑清隆
音乐上的交流和志向上的共鸣,让翁顺砚和广濑清隆彼此欣赏与信任,也正是通过广濑清隆,翁顺砚第一次知道了位于菲律宾宿务的一所孤儿院,知道了那里的孩子境况并不好过。
40多个男孩,要共用一个卫生间和淋浴头,床上连床板都没有,只有几根铁丝杆,晚上睡觉就直接睡在铁丝上,更别说去好好上学念书…
在听说菲律宾孤儿之时,翁顺砚的母亲刚刚逝世不久,至亲骤然辞世的打击让他陷入了痛苦与悲伤,也让他对“孤儿”这个词充满了感同身受的同情。几乎是在一刹那,翁顺砚下定了决心——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去帮这些孩子。
2016年3月,当他筹划着和广濑清隆同赴菲律宾看望孤儿的行程,恰好又赶上了中、日、菲三国领土争端闹得最凶的时候。在一些人看来,此时出国去做这样一件事,完全就是“和一个敌国的人去帮另一个敌国的人”。对于翁顺砚的父亲来说,妻子刚刚去世,儿子就要离开上海去菲律宾,他的内心也有些无法接受。
面对旁人的质疑和亲人的不解,深信“善良不分国界”的翁顺砚,还是毅然进行了这段旅程。
当他和广濑清隆出现在孤儿院里,为他们拉琴、送去礼物、带他们玩耍游戏,这些从来没亲眼见过小提琴的孩子沸腾了,有些甚至流下了眼泪。在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第一次被这么多爱与温暖缠绕。
翁顺砚、广濑清隆和孤儿院的孩子们互动
其中有些孩子主动找到他们,羞涩地询问“你是否可以做我的爸爸”,在这些孩子的生命中父母的身影一直缺失,可翁顺砚和广濑清隆的出现却让他们感受到了亲人一般的温馨亲切。
“那种感觉真的是……你没有去到现场,就没办法体会到那样的感动。” 翁顺砚微笑着回忆道。
翁顺砚给孤儿院的孩子们拉琴
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1月,翁顺砚已经进行了四次菲律宾之旅,去看望和陪伴那些孩子,或是给他们演奏,或是教他们拉琴。在看到他带回来的照片和视频之后,原先有过疑惑的人们也慢慢开始理解这份跨越国界的关怀与爱。
而翁顺砚也表示,不管旁人如何看待,自己都会努力将这个慈善之旅进行下去,和孩子们之间来之不易的情谊,也是他最珍惜的东西。
有人说
只有体会过磨难与困境的人
才会对他人遭受的苦难更加感同身受
也会更加珍惜生命中一点一滴的善意
而爱与音乐这样美好的事物
原本就是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东西
这个颠不破的真理
翁顺砚已然用亲身经历证明
推荐阅读: